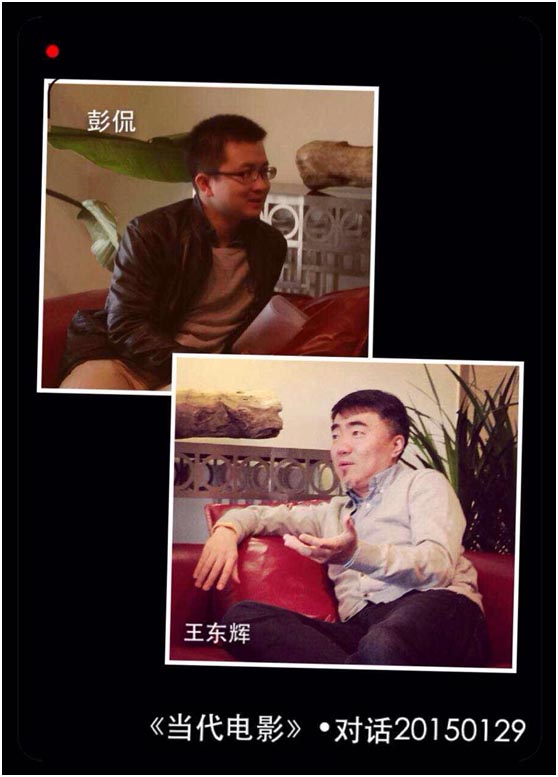| 中文|ENGLISH |
 |
| 尊重创作的“创意制片人” |
|
尊重创作的“创意制 片人"
时间:2015年1月29日上午 地点:合力映画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对话者:王东辉(独立制片人) 彭侃(电影产业研究者/清华大学博士研究生) 来源:《当代电影》2015年第3期 责编:向竹
CAA的五年“受益匪浅” 彭侃(以下简称彭):王总,您进入电影界到现在,已有将近十年的时间了。这十年也正是中国电影真正走向产业化、市场化的十年,中国已经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电影市场。结合您的从业经历,您认为这十年给您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 王东辉(以下简称王):一切都发展太快了。最早我们拍《第三个人》的时候,几百万元的投资都谈了很久。前两年上映的管虎导演的《杀生》,早在多年前就开始筹备,400万元的预算却一直找不到投资。但如今,非常多的热钱在涌入整个行业,这个过程很戏剧化,发展真的是太快了。 彭:我们知道您2005年就进入了知名的好莱坞经纪公司CAA在中国的分公司任职,您觉得CAA的经历对您后来成为制片人有怎样的帮助,因为据我的了解,CAA是一家在好莱坞非常有开创性和影响力的公司。它不是单纯的人才经纪公司,而更像是项目整合运营商,比如他们会先找到一部引人入胜的文字作品,再提出一整套的电影企划案:包括剧本、制作人、导演,最后将这个项目打包卖给制片厂。这种运作方式有在中国实践吗? 王:CAA刚进入中国的时候,中国电影业才刚刚进入产业化的阶段。那时候的经纪公司主要是签演员。在CAA之前几乎没有经纪公司会签约导演、编剧的。只有“华谊”尝试过签陆川、路学长,但也只是签,签完了也没有具体实施到工作当中。而CAA是那时候最早把签约编剧和导演制度带到中国的。后来CAA也有在中国尝试类似于好莱坞的模式,CAA把班底签约好,再去寻找投资的项目,比如有部电影《夜店》,导演、编剧是CAA签约的杨庆,演员也是CAA的李小璐、徐峥、张嘉译,“打包”后一起拉投资。宁浩的《无人区》,从宁浩到黄渤、徐峥、余男,也都是CAA自己的签约艺人。 CAA比较厉害的地方就是他看到这个行业的本质,就是先抓内容,在当时中国没有任何一个公司跟编剧和导演合作的时候,CAA愿意花这个投入。跟编剧和导演签约,其实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拿到第一手内容,然后提供给自己签约的演员。当然这种提供不是单向的,一定是双向的,因为好的演员也会带来好的项目,提供给自己公司内部的编剧和导演。 其实在CAA做经纪人,就有制片人的职能在里面,像对剧本、对故事的选择,跟导演的沟通,搭配演员,然后去跟投资方沟通,预算的情况等这些事情,其实就是制片人前期的工作。 彭:您选择于2010年离开CAA,当时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王:2009年底的时候,从我个人做经纪人的角度说,高群书的《风声》票房破亿元,黄渤和管虎拿了两个“金马”。于是我开始想尝试进入到制作行业,由于我是高群书的经纪人,他正在筹备《一场风花雪月的事》,这是一个契机,我们两人一起做了导演工作室。 随后,我和高导合作了《神探亨特张》和两部电视剧,之后就单独出来自立门户了。 彭:您之前在英国学习电影,然后在CAA做经纪人,整个的背景是很国际化的,那么在您操作这些电影项目的过程当中,您是否会格外看重海外市场? 王:《绣春刀》就有考虑过。当时也是因为古装动作片在海外有一定的市场,包括张家振作为监制,他在海外销售上也给了影片很大的帮助。去年我们在戛纳电影节的时候,剪辑了一版预告片,就卖出去了海外版权。《绣春刀》的北美、东南亚、日本、韩国、俄罗斯版权都卖出去了,新加坡和澳大利亚已经上映了,其他国家和地区应该是发行DVD。 这种市场反响其实是比较难得的,因为很多中国电影到戛纳其实是“撑脸面”去了。片商不知道演员是谁,不知道导演是谁,类型又不清晰,怎么能够卖得出去?除了古装动作片,其他任何一个类型片都需要观众对中国文化特别了解才能看得懂,比如浪漫喜剧爱情片,老外看不懂,所以基本都卖不出去。 尊重创意 不迷信“大数据” 彭:找到适合开发的剧本,可以说是制片人的首要任务。在您看来,挑选剧本有没有比较明确的标准? 王:看剧本主要是靠经验,看得多了,自然就知道哪一个剧本好,哪一个不能继续进行。以前当经纪人的时候,特别是带黄渤、张嘉译、李小璐的时候每天接触的剧本太多了。书读多了,你自然而然就有那个感觉,就不用再每次去看有几幕,有故事结构、人物,看完之后,大脑里面就会反应出来对这些内容的评估。 大家都说国内特别缺这种好剧本,其实在好莱坞也一样,可能好剧本的比例稍微高一些。作为制片人,没有办法,只能在茫茫剧本中寻找好的项目,否则这个行业就没有办法发展下去了。 彭:的确,剧本可以说是整个电影制作行业的根基所在。如果没有能吸引观众的故事,一切花招都是白费。所以在好莱坞,每年花在剧本开发上的费用就高达九亿美元。中国电影业近年来对编剧的重视程度也在逐渐提高,尽管离好莱坞还有一定差距。我们可以注意到中国电影业在剧本开发方面也在浮现出一些新的趋势,比如一些网络文学作品被开发成电影,或者来自于别的领域的IP,像综艺节目、游戏等被开发成电影,您怎么看这个跨界开发的现象? 王:这种现象是由于我们自己编剧的成熟度不够,原创的东西太少。当然这种“嫁接”的方式在全世界各个地方都存在,因为文学作品是有基础的,在它的基础之上再改编,效果会更好一些,成功率也会更高。如果做这种开发,还会涉及到现有作品的版权问题,用哪种合作方式,买断还是合作,都是制片人需要思考的问题。 彭:在挑选项目方面,您对创作者会有怎样的考量?比如是否会优先考虑像路阳这种能编剧能导演的“作者型”创作者? 王:相对而言,我比较喜欢编剧写好剧本之后,导演在编剧的基础上再做自己的调整,这样是“1+1大于2”的过程。如果完全都是一个人的工作,他不容易“跳出”自己的漩涡,还得花很长的时间去跟导演沟通,去说服他做出一些跟市场更符合的东西。 彭:在挑选剧本的时候,您会有类型的偏好吗? 王:这倒没有,各种类型都可以,而且什么类型都要尽量去尝试。最重要的是,制片人要对这一类型项目做出准确的市场评估。不管是什么类型,都还是以故事为基础。 我们在挑选项目时会调研这一类型电影在以往市场的表现,但这个数据并不是绝对的,而是要看这个类型在市场上占有多少的份额,它最好的表现和最差的表现都是什么水准,然后再评估自己项目未来的预期,随之倒推出自己的制作成本。 彭:您提到了运用数据帮助进行项目评估。在好莱坞的产业体系中,数据分析是很重要的一环,甚至很多好莱坞大制片厂的高管就是做市场调查出身的。在中国,数据分析,尤其是“大数据”也是当下中国电影业特别火热的概念,您是如何看待的? 王:“大数据”只是一个概念,我们能够从中了解这个行业的大致方向是怎样的趋势。但电影毕竟是一个结合体,一半靠的是商业模式的管理,另一半是它的创意,而大数据对创意这部分来说,没有任何的意义。电影心理学说,我们永远不知道观众喜欢什么样的内容,因此在创意上,我们一定要基于目前的状况再往前走一点,但“往前走”就一定是有风险的。大数据无法提供这些东西,数据只能提供历史的内容,但数据所指向的任何趋势是每天都在变化的。 彭:在这一点上,我的观点可能跟您有些不同。从好莱坞的实践来看,数据分析在帮助制片方了解观众,调整他们的创意策略方面还是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的。比如在剧本开发阶段,好莱坞片厂就会召集观众,进行概念测试、标题测试和定位研究等等一系列的调研。在电影剪辑完毕后,也会举办一系列试映活动,调查和分析观众对影片的反应,并根据观众反应对影片内容进行调整,实践证明还是挺有效果的。 王:其实我并不反对适当地运用数据分析,但我不同意本末倒置地用数据来决定创意。比如以前我在跟各个公司谈项目投资的时候,他们都会把宣传和发行意见放在一个项目决定性的角度,我说这完全就错了,宣传和发行他们都是市场操作环节,是我们创作出产品之后,交给他们,让他们把这个东西销售出去,卖给观众,而不是说我还没有做这个东西之前他们就告诉我这个东西能不能做,应不应该做,那这个关系完全就反了的。 彭:听得出来,您还是比较偏重创意的发挥的,感觉您似乎遵循的更像是好莱坞的独立电影制作的思路? 王:是的,从创意这个角度出发,独立电影这种创作模式是更适合我的。基本上是在前期创意已经确定的前提下才去拿给资方,再去跟资方说我有这样的项目,你愿不愿意投。对于资方来讲他只是评估这个项目的投资风险而已,他做Yes或No这样的答案,相对来说比较简单,我的项目的成活率也会很高。如果是大的制片厂,比如好莱坞六大公司,每年死在它们手里的不下上千个剧本,而且他们完全拥有版权,说不拍就不拍了。 但对于一个创作人员来讲,不论是对于制片人、编剧还是对导演来讲,花了心血写出来剧本,最终还是希望要呈现给观众的。 每种类型片都有自己的份额 彭:作为一位独立制作人,通常的操作模式是选中一个项目后,好好培育它,培育成熟后再找投资方。是否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开发项目的过程,比如《绣春刀》这个项目,在筹备的过程中,如何和导演路阳合作,一起把项目发展起来的? 王:当路阳通过朋友把《绣春刀》的剧本给我的时候,已经是他的第六稿了,写了两年了。我看了剧本,确实不错,而且也看了路阳以前的电影《盲人电影院》,觉得他很有才华,便约他面谈,提出来我认为这个剧本有哪些方向上的问题,如果他愿意跟我合作的话,我希望我们一起来对剧本做一个调整。他同意了,接下来,我们花了八个月的时间,又调整了四稿,每次坐下来都会一对一地沟通,从头到尾地对剧本进行讨论 在剧本完成之后,我找到了张家振先生,邀请他出任这部电影的监制。他也挺喜欢这个剧本的,同意帮忙。同时我也将剧本递给了张震,他看完之后也挺认可。那么这个项目基本就成型了。 彭:筹备过程看起来很顺利,但是听说后来的融资遇到了问题? 王:因为那一年的几部古装动作片都非常不成功,包括《血滴子》,所有的资方都认为这个类型片在市场上中国观众已经看疲惫了,已经厌倦了,他们对这种类型片都比较慎重。但我是不相信,市场的实际情况不应该是这样的,因为它对每个类型片都应该有自己的一个固定的份额和固定的观众,不应该因为两部片子去否定这个市场的份额,所以当时苦口婆心跟各种资方在沟通,最终成功取得了投资。 彭:我觉得您的这个观点很有意思,就是每个类型片都应该有自己的一个固定的份额和固定的观众,从这个角度看,对制片人来说可能选择哪个类型其实并不是那么重要,因为每一种类型都有可操作的空间。但业内也有另一种做法,就是有意识地去追寻一些热点的类型。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王:无论是在电影行业还是任何一个行业,追风是最有风险的,因为你永远是在潮流后面追。对我而言,我不去管潮流是什么样,先把我的故事做好,只要这个故事能吸引到合适的演员,制作成本是在这个市场的安全值里面,在我的估算之内就可以做。 彭:对于制片人来说,如何控制这个项目的成本,控制它的风险。比如《绣春刀》,这个项目投资大概三千万元左右,您当时是怎么样去考虑它的成本和风险这些问题? 王:当时跟资方谈的时候,对之前五年古装动作片整个市场做了一个调研,对于每部片子的盈利情况也做了调研,还对每部片子的票房和它的成本比例做了调查,再通过中国每一年市场份额的递增,反推过来,算出预算的安全值是多少。最开始的时候,路阳说1500万元就可以拍,我说这不可以的,因为要拍出一个有品质的电影,确实是要有一定的资金要求的。3000万元的预算已经是相对保守了。 彭:《绣春刀》电影上映后,获得的口碑很好,但是市场表现不是特别好?您觉得主要原因是什么? 王:我觉得主要的原因是在影片进入到后面市场阶段的时候,整个的营销和发行都没有到位,包括整体宣传的铺垫、上映时候的物料准备,上映首周末的银幕数量等都不是很理想。在某种程度上,因为我和路阳都是新人,我们对创作上愿意承担很大的责任,但是到后端进入到市场的时候,我们是没有太多的话语权的。 国内融资渠道尚狭窄 “完片担保”难落地 彭:您对目前中国电影行业的融资环境怎么看?现在市场上的资本来源相对来说已比较多元了,除了传统的像“中影”这样的国有电影资本,像“华谊”这样的民营电影资本,还有像银行、基金等金融资本,以及从其他行业涌入的热钱等。从您个人经验来说,您更偏向于跟什么样背景的资本去合作? 王:我从做经纪人的时候就和各种各样不同的资金接触,包括自己独立出来之后,圈内的资金基本上都有过接触。但其实,接触完一圈下来之后,合作比较通顺的基础是什么?是无障碍的沟通。我说出来前半句,他知道你的下半句是什么意思,这就降低了“沟通成本”。 当然,要说什么资本最适合合作,真正能合作的还是业内的资本。 有些新的热钱进来之后,说出来的内容,提出来的那些要求,真的是让你哭笑不得。你会花很多的时间去跟他解释,跟他说明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很多资本完全不了解这个行业就要进来,我觉得这是挺危险的。 彭:的确,跟业内资本方沟通起来,可能是最容易的。很多行业外的热钱他们对电影业的投资很大程度上带有“玩票”或“赌博”性质,既难沟通,也不稳定。但我也注意到,在好莱坞除了业内资本外,华尔街的金融资本与好莱坞的关系也是非常密切的。比如很多华尔街的投行都对好莱坞的大制片厂进行“拼盘融资”,很多的银行给予电影项目“贷款”等。但目前银行等金融机构对中国的电影业介入还很浅,您认为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差距在哪里? 王:可以说中国股票市场和美国差多远,中国电影的金融资本市场就跟好莱坞差多远,从整个资金体系的成熟度看,目前中国的银行贷款还是“当铺”的方式,把东西押出来,才能给贷款。但在国外,公司可以用自己的知识产权做抵押,而中国的知识产权的衍生价值只体现在了票房上,没有后续的体现。对于银行来讲,我评估不出来你这个东西值多少钱,我怎么去贷给你多少钱,所以很难实现。 当然像“华谊”这样的大型公司它们与银行的合作是相对成熟的,因为它们有很多除了电影以外其他的业务板块,是可以自己给自己担保的,用左兜的东西担保右兜的东西,银行是可以的,你右兜拿不出来,我就拿你左兜里的东西给补回去,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像国外这种独立制片人自己运作项目,通过海外市场的预售,然后拿去银行做抵押,再加上一部分税务的补贴,最后完成这部片子整体的融资,在中国还实现不了。 彭:您最近应该也注意到一个消息,全世界最大的完片担保公司——美国电影金融公司在上海自贸区成立了中国分公司,准备拓展中国的业务。在美国,完片担保制度其实是特别重要的一个制度,尤其是对于独立电影来说。但很多人担心该制度在中国没有办法落地,您怎么看这件事情? 王:完片担保就像是保险公司,买了保险,就一定在这个周期里面按照预算拍完,如果无法完成,保险公司就可以进入到执行层面上,把所有人都换掉,这就是完片担保公司的作用。 在国内,完片担保还稍微早了一些,首先我们的行业体制不一样,在美国电影是产业化非常高的工业体系,它以职业经理人为核心,也就是“制片人中心制”,大家按照明文规定的游戏规则在走。开机之前,所有的预算大家都已经确认过了,每一项花多少钱都是“透明的”,在执行过程中,承制方按照预算支出就可以了。但国内还是基于“导演中心制”,尽管这两年在慢慢转变,但所有从业者要从这个根深蒂固的观念体系里走出来,的确需要时间。就是说,目前,中国电影业还没有办法百分之百遵从好莱坞式的游戏规则去工作,这样的话,完片担保公司要承担非常高的风险。 其实还有很多海外的公司都在中国设有分公司,刚开始可能都会遇到“水土不服”的问题,即便是世界五百强的企业,到任何一个地方也都面临着如何去“本土化”的难题,更何况文化产业,要做到文化上的本土化就更难了。 彭:的确,完片担保制度本身是一种非常有用的制度,但可能在中国的落地还需要比较长的一段时间。我曾经采访过美国电影金融公司的副总裁詹姆斯•加耶戈斯,他就提到,可能伴随着中国电影融资结构的进化,中国电影对保险的需求才会爆发出来。随着中国电影的品质不断提升,相应地,成本也会不断上涨。到一定阶段,股份投资者可能会希望利用银行借贷使他们的投资发挥杠杆效应。像世界其它地方的电影市场一样,银行会以合理的利率为电影提供融资,但它们会要求资金安全,这时候便是电影保险大显身手的时候了。而目前银行等金融机构对中国电影业的涉入仍然较浅,因此对电影保险尚缺少硬性需求。 要“名”还是“利”: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彭:如您之前所说的,目前,中国还是没有摆脱以导演、创作者为中心的体制,还不是完全按照市场规律行动,而很多时候,中国电影创作者是出于个人的某种情怀或是兴趣去完成项目,而不是面向市场,面向观众去完成项目。那么在您作为制片人操作项目的过程中,有什么样的一套方法去扭转这种局面,怎么样跟这些导演打交道,让他听制片人的话? 王:在接触项目之前,和导演要有充分的沟通,有的时候导演能够接受这种操作方式,有的导演确实就没有办法接受这种方式。从制片人角度来讲,需要寻找一种折中的办法。 在美国,大家对“制片人制度”的认识已经根深蒂固,导演也好,制片人也好,大家都知道自己的那条线在什么地方,但是中国就是因为没有制度,都是模糊的,所以只能去试探那条线在哪里。这是一个博弈的过程。 同时,我觉得制片人不能只和一个导演合作,这一定会有问题。因为我是一个经纪人,从投资风险来讲,把所有鸡蛋都放在这一个篮子里,导演的创作周期也有高有低,他没有办法保证每部片子都一定是很好的,在世界电影史上也没有这样的导演,一辈子拍的所有影片都非常成功,这是不现实的。那么从制片人角度来讲,就要想办法把鸡蛋放在几个不同的篮子里,去分担作为制片人的风险。 彭:我个人感觉,制片人跟导演的这种关系在整个项目过程中是会发生变化的,比如在前期筹备阶段,导演还是比较会听制片人的意见,尤其是在融资阶段,因为他在这方面没有太强的经验。但是到了拍摄阶段之后,导演的那种创作意识就开始涌现上来,制片人说的话他可能就不一定会接受了。会不会存在这样一个局面? 王:会的。 彭:我也曾经听到很多传言,一些导演、编剧,他的电影可能今天要开拍了,剧本还没有出来,不知道这有没有夸张,类似于王家卫这样的导演,遇到这样导演的时候,制片人怎么办? 王:那就只能“忍”了。电影分两种,一个是就冲着市场去拍,另一个是想通过电影去表达一些东西。那么无论是导演也好,制片人也好,还是投资人也好,都一定是对电影有很强的情怀,大家才愿意去拍电影。因为电影不是用来发家致富的行业,像王家卫这样的导演,像李安这样的导演,你和他们合作的时候,你相信最终完成的作品是完美的,就是他的情怀,制片人就要去认可这方面的事情。 所以在这个行业里面,不要想鱼和熊掌都兼得的事情,是要“名”还是要“利”,要先分清楚哪个是主要的,然后再去判断这个项目是要做还是不做。 任何一个项目,都要有一个最基本的保障,在这个前提下,稍微地往哪个方向去倾斜而已。没有人保证能够获得利益,如果“一刀切”说一部电影只是奔着“名”而拍,但是没有人会保证就一定有“名”。这是一件很微妙的事情。 彭:总的来说,制片人还是很难充当的角色。因为他要在艺术和商业间保持一种微妙的平衡。一方面要给创作者空间,一方面也要考虑成本。一方面既要有沉下心去洞察、打磨好作品的定力,另一方面也要有长袖善舞、整合资源的实力。 保证资金不断流:制片人的首要职责 彭:进入到拍摄阶段之后,作为制片人,要发挥的作用还会侧重在创作层面吗?还是会转移到控制预算、保证资金等方面? 王:如果进入拍摄阶段,因为电影的投资基本都是分期投入到项目中来的,那么制片人主要工作是保证资金不要断。其实现在中国电影很多项目拍戏拍到一半资金链断了,前几年更是这样,拍了一半都停机了,但是《绣春刀》没有。没有什么特殊的秘诀,就是要和各个资方一定要搞好关系,这样资金更容易到位。 因为任何一个电影项目一定不是一家公司投资,而是几家公司一起投资,不仅是资金的投入,还有资源的互补。在这种情况下,制片人面对着很多资方,然而各个公司内部的财务流程不一样,每个公司的个性也不一样,所以制片人需要做出周到的安排,并且要保持灵活性。 彭:在拍摄阶段,对于控制成本,制片人会进行哪些具体的工作? 王:这个其实在于前期筹备工作的时候做得是否详细了,每天拍摄的内容,每个场景怎么拍,如果你前期筹备把这些工作都计划好了以后,到拍摄的时候就很简单了。我们计划是这样的,你可以有限度地改,不能改得太大,以此作为一个基准,然后大家去工作。否则的话,如果你前期筹备工作没有做得仔细,而是你好我好大家好,一团糊涂账,那拍摄的时候一定是有问题的。 彭:但前期筹备到这么细致的一个程度,中国的很多电影项目应该还是没有做到吧? 王:对,因为整个行业的专业程度还没有那么高,所以大家都在探索,都在学习。但大家都已经认识到如果前期筹备得越详细,拍摄的时候也会越顺畅,工作起来也会越顺。 彭:当电影制作完毕,进入到发行阶段时,独立制片人的角色是怎样的? 王:如果在美国,制片人到这一部分就不用管了,被知会就可以了,知道发行公司会保证市场的宣发成本,第一周要有多少块银幕,制片人不会再介入到非常细节的东西。因为有专业的宣传公司,有专业的发行公司都去对接了。但是中国还不够成熟,制片人这一部分也要努力去参与,去制定计划,包括上映之后自己想办法去增加排片,去想方法做一些营销。 彭:从好的方面看,这可能也意味着在中国,对于制片人的锻炼比起好莱坞是更加全面吧。在最后的资金回收阶段,制片人的角色又是怎样的呢? 王:到了资金回收阶段,主要是由发行方负责了。 彭:在好莱坞,资金回收会特别讲究回收的顺序,比如有的投资方会事先要求回收自己的这一部分投资,在中国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王:中国现在还没有美国那么复杂,大家都是风险共担,同进同出,这是一般常规的做法。收入汇聚到发行方那里,再按照比例进行分配。 彭:在中国电影项目回款这方面,目前相对来说已经比较规范了吗? 王:还不是太规范,周期会特别长。当然我相信会越来越规范。整个中国电影行业的契约精神目前来说还是在逐步增强,一般还是会按照合约去执行。 成为创意型的制片人 彭:今天这个采访,除了探讨制片人的角色之外,编辑还交给了我一个任务,就是要了解像您这样的年轻制片人的心路历程以及生活状态。您是否回顾一下您对电影的梦想是怎么样产生的? 王:这可能跟小的时候我爸带我去录像厅看录像有关系,后来就演变成一发不可收拾,通宵通宵地看电影。80年代,家里面刚买录像机,我爸为了让我呆在家,就给我办了一个租带证,我记得特别清楚,是150块钱人民币看100盘录像带,然后在一个小本上记,我一个星期看完了,让我爸很惊讶。我基本上是早晨计算好一天能看几盘录像带,到录像店晚上下班之前,把这个还回去,然后再拿几盘回来,再看到第二天早晨,录像店上班再去换新的,一个星期就把100盘看完了。基本上什么类型电影都看。 彭:您是如何决定走上创业成为一位独立制片人这条道路的? 王:因为我开始工作的时候已经比较成熟了,所以我是属于那种稳健地一步一步前进,一个速度一直坚持往下走的类型。对于工作,我是属于主动型的,我明确地知道我想做什么,就闷着头儿一直往那个方向走。 彭:创业之后的生活状态跟此前的生活状态有变化吗?能否描述一下在常规的状态下你一天的工作日程是怎么样的? 王:基本上是早晨九点多钟到办公室,查邮件,回邮件,这些事情做完基本上午就过去了。下午如果可以的话,就要看一些发过来的剧本,或者和编剧开会。如果上午还有没有处理完的事情,也会放到下午。一早一晚,还会和美国开一个电话会议。基本上每天工作都要超过12个小时。 彭:听上去挺累的。很多在校的学生也好,还是新的电影人也好,都想进入到制片人这个行业里。您认为该如何判断一个人有没有做制片人的潜力,要有很广的人脉还是专业背景要很强大,还是说要有资本的支撑? 王:最主要的是先在外面磨炼四五年。经验很重要,人脉很重要,做事情的态度更重要。 彭:您目前有什么新的制片计划正在筹划吗? 王:现在有多个项目在筹备当中,有差不多十个左右。包括与《狮子王》的导演Rob Minkoff在合作他的中美合拍的新项目,预计今年下半年开始拍摄。与金依萌导演在合作一部心理惊悚的类型片。另外还有我自己希望开发的一些类型片项目。 彭:您对自己未来的规划是怎样的?是坚持走类似于美国独立电影公司的道路,去做好看中的这些项目,还是也会考虑跟大的电影公司去合作? 王:就目前的情况来讲,我还是走独立制片人的道路,先去开发自己喜欢的电影项目。等开发出来,最后还是要和那些大的电影公司合作,不过项目前期这一部分还是想自己做。我觉得大公司里面的制片人更多是行政上的角色,独立制片人更多关注项目的开发培养和整体的策划。 我觉得自己更适合做创意型的制片人,比较享受找到好玩的故事,与创作者、编剧一起聊故事,把它一点点雕琢出来,变成一个可以拍摄的剧本,然后往前推进,我对自己的定位是这种类型的制片人。
|
Copyright © 2009 - 2017 CDP All Rights Reserved
网站制作:沈阳全景网络科技www.024360.com